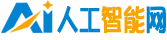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《天人五衰》

美国作家唐纳德·里奇(1924-2013)。
有一种书,初见时未必能参透其文本背后的真意,再翻开时,却相见恨晚——唐纳德·里奇的《日本日记》就属于这一类。大约十年前,我因写一篇文章,匆匆翻过此书,文章写完便束之高阁了。
唐纳德·里奇(Donald Richie)出道早,名气大,是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电影之第一人。其本人作为学者卓然有成,他的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研究,即使在日本学界,也是必读书目。1975年夏天,荷兰作家伊恩·布鲁玛甫抵东京,便先拜里奇的码头,尽管“我后来得知,唐纳德·里奇不认识汉字,也不会日语”。后来,布鲁玛自己的回忆录《东京绮梦:日本最后的前卫年代》出版时,扉后题记就写着“纪念唐纳德·里奇、诺曼·米本和寺山修司”。
《日本日记》是一部有分量的大书。全书按年代顺序分成两卷,上卷从1947年写到2004年。原则上,下卷应该是从2005年写到作者去世的2013年。之所以说“原则上”,是因为到目前为止,只出过上卷,中文版系对Stone Bridge Press社2005年英文版的迻译,包括日记在内的作者全部手稿,现藏于波士顿大学霍华德·葛列卜档案研究中心。这部书名为“日记”,其实是以作者早期的手记为蓝本,对过往人生的回忆。从时间上来看,上卷基本涵盖了日本战后六十年,内容极其庞杂,涉及众多的文艺名人和社会文化事件,有大量的一手资料,对战后日本文学史、文化史和电影史研究,有重要参考价值。其中,对与三岛由纪夫的交游,作者记述甚详,且有不少独家爆料——倒未必是刻意“爆料”,也是出于美学,甚至性趣味上的惺惺相惜,二人之间显然有种超出普通友情之上的情感连接,有助于我们立体地读解三岛这位谜一般的小说家的艺术人生。
唐纳德·里奇著《日本日记:1947—2004(上)》。
1949年春,里奇离开日本,回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。1952年初冬,里奇接到朋友、人在哈佛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梅雷迪斯·魏若比的电话,“让我照料一位刚到纽约的日本青年作家”。于是,在纽约而不是在东京,里奇第一次见到三岛。三岛是作为《朝日新闻》的特约记者,赴美旅行采访,“我那时不懂日语,他的英语还不像后来那样地道。尽管如此,我们设法交流得让我足以明白他的愿望”。三岛的愿望清单倒也简单明了:想看纽约所有的塞巴斯蒂安像,去大都会歌剧院听施特劳斯的《莎乐美》,再去一间真正的同性恋酒吧体验一把。关于最后一点,作家的理由是,其小说《禁色》中,涉及那类场所,“他希望比较、评估,并捕捉地方特色”。三岛给里奇的第一印象是“谦恭有礼——我见过的人数他最有社交礼仪”;其次,是“他对内在一致性的坚持。跟三岛一起,就是参演一出戏”。有了这个由头,里奇与三岛的交情自然变得亲密起来。
1954年初,里奇从哥大毕业后回到日本。梅雷迪斯也来到东京,正在翻译三岛的《潮骚》,仨人常聚会。此时,三岛的英语突然变得很好,有时甚至帮忙翻译。随着交往的日益浓密,里奇对三岛有了更深层的了解。譬如,他觉得三岛是一个花花公子,“但他的衣着好,不炫耀。你要是近观,会看到裁剪出众,料子一流。他像德川时代身穿朴素和服的那些商人,衣服衬里价值不菲”。对此,里奇觉得是“当局禁止表现”,或“三岛律己很严”。但其实,这是江户时代武士贵族阶层的一种生活品位,所谓“uramasari”,即穿衣重表更重里:表露在外面,舒适体面即可,而衬里是穿给自己的,才更需高级感。那时,塑型瘦身已经提上作家的日程,他甚至开始练起了拳击,“三岛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他渴望的形象,所有脂肪和所有冗赘全都融化:灵与肉合一——一副消瘦坚硬的身体装着一颗消瘦坚硬的心”。
里奇对三岛的记录,散见于很多年份,其所扮演的角色,颇有些像电影摄制组的场记,他甚至记录了作家在后台的下意识“表演”,或者说一些表演花絮。里奇常在后乐园健身房的训练课上跟三岛见面,“一间健身房更像一间肉店——很多好肉”,其中的一部分属于三岛。不过,三岛的肉身重塑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,在里奇眼里,并非一向完美:“我常看他苦练自己的上半身而忽略了下半截,肌肉结实的躯干架在细长的腿上。”下课后,众学员一起在浴场洗澡,一般都会争相跳进那个盛满热水铺着瓷砖的大浴池,然而三岛从不:
他独自淋浴,前身得体地转过去,毛巾围在适当位置,然后穿回紧身内裤,一成不变的棕褐色宽松裤子,黑色线衫,颈上一条金链。然后朋友一般挥挥手,匆匆一笑,这位健身的作家消失了,直到下次再来。
1955年,三岛带里奇和梅雷迪斯去他新开发的一家法国餐馆,“他告诉我他要改变风格,他现在很欣赏森鸥外”。可里奇觉得森的风格硬朗、舒畅、厚重,迥异于三岛的装饰风格,内心对三岛的急转弯多少有些不解。后来梅雷迪斯告诉他,三岛其实是受到当时的现象级畅销书《太阳的季节》的刺激,“由纪夫觉得这应该是他的份”。果然,三岛不久即发表了“硬朗、酣畅、厚重”的小说,即《金阁寺》。那次饭局,使里奇意识到自己“正在目睹一项进程的部分发展——由纪夫不断转变的生活,他对自己的持续再造”。
在那座位于东京马込的西班牙殖民风格的豪宅——“白亚”馆的派对上,作家主人明星范儿十足:
我们听到他在我们头上的笑声,然后他来到我们中间确认酒已斟好,招呼每一个人,在我们中间周旋的时候魅力四射,主要用英语谈话。这是因为客人多为外国人或在海外住过的日本人。原因之一当然在于很少外国人讲日语,很少日本人说外语。不过,另一个原因,是三岛喜欢控制听众。
但里奇注意到,派对自始至终“没见到他的妻子,可能在厨房恪守妇道”。这使他联想到瑶子夫人出现在社交场时的情景,“当他带她出去,他关怀备至,但在家里,她变得更像一位日本配偶”。
洋范儿如三岛作家,自然也少不了与老外朋友交流对欧美文学的看法。里奇知道三岛极不喜欢海明威,尽管“两人都是风格独特的作家,都是浪漫主义者,都爱展示男子汉气概,都是过时准则的拥护者”。可并不妨碍他“开始钦佩这人本人。那是这桩自杀博得他的尊敬,还有自杀时的果断”。他向里奇确认道:“嘴里的来复枪,拉动扳机,听说是用大脚趾。没错吧?”
1965年4月,三岛请里奇去大映片场。“在一个看似能剧舞台的布景之中,三岛穿着一套战前的陆军制服,帽子在他前额拉低,正在佯装切腹。这是最后一场的最后排练。”里奇与三岛的见面过于频密,以至于他有时分不清哪些是舞台上,哪些是舞台下。
1967年冬,里奇在位于六本木的花园雪地上,目睹了三岛的一场实拍:“摄影师裹着围巾和毛衣,作家则一身赤裸,除了一条白色的兜裆布。他还挥舞着一把剑,摆着不同的姿势。所有这些姿势显出武士的某一极致。”里奇受到震动,待外景实拍结束后,他从三岛的原著《假面的告白》中查到了片中情节的原始文本:
我闪开了。一阵原始的肉欲在我的心中燃烧,在我的脸颊打上烙印。我觉得自己用水晶般透明的眼睛盯着他……从那时起我爱上了近江。
三岛在举事前夕,明显加快了进程,以至于“所有的朋友比平常更多见到他。他电话打得更多,给我们写了更多短函,更多关心。当他和我见面,我们更少闲聊。他反而谈着作家和写作”。里奇说“你应该竞选公职”,三岛做了个鬼脸:“一个作家不能像个政客。瞧瞧石原慎太郎,他两者都不是。一个作家能做的就是有所展示。”
在三岛即将杀青最后一部长篇——四部曲《丰饶之海》之四《天人五衰》时,里奇问他接下来准备做什么。“我不知道,”他说,“我想我能说的都说了。”待了会儿,他又说道:“我正在完成的这部小说很难。我不知道它要怎样结束。我没主意。我不知道怎么做。”见里奇未吱声,三岛继续说:“很奇怪,但我害怕结束这本书。”里奇大惊,“因为我从未听三岛说到害怕”。
所以,在三岛自戕后,里奇应邀为英文《日本时报》写文章,他也的确无从谈起。因为在他看来,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连续的进程,死不过是最后的完成罢了:
死得这么戏剧,就像三岛任何一出戏剧的情节那样耸人听闻,对于以如此惊人的方式终结生命的一个人,可谓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。这就是当我听说三岛自杀时所想到的。并不惊奇。在这之前,他频繁说起自杀,我多少习惯了这一可能。他更多地说起它,是因为我们见面更多了。
三岛虽然退场了,但里奇与三岛的故事远未结束。1983年夏天,里奇陪好莱坞大牌导演弗朗西斯·科波拉拜会三岛遗孀瑶子夫人,谈科波拉的一个项目——拍一部三岛的传记片。但双方分歧过大,“她要的是最近这些年她一直涂抹的伪君子,他们要的是一部讲述一点真相的商业片”,项目遂无果而终。
半年后,里奇又陪另一拨好莱坞影人——保罗·施拉德和玛丽·贝丝·赫特跟瑶子夫人吃饭。“好一阵子她一直在为丈夫澄清——禁映他的影片《忧国》,跟他从前的朋友断绝关系,否认一些事情——为了把他塑造成她觉得他应该是的人。……有一天的午餐非常激烈——眼泪,我明白。”核心问题仍在于三岛的性取向,“她本应最清楚,现在否认它”。好莱坞导演当然不可能过滤掉这个猛料,但瑶子夫人的眼泪也可以理解,“因为他们的女儿不知怎么拿到一份剧本,立刻吓着了”。瑶子夫人尤其不想让保罗导演见里奇,说“他不能信任”:
这毫不奇怪。我知道得太多了。还有,我没站在她那一边,因为众所周知我一直在批评这位杰出而且现为圣人的作家。
对此,里奇认为三岛夫人“说得完全没错”。作为很早就毅然出柜的著名同志,“我了解三岛,我不想参与她现在对他的粉饰,而死者已无能为力”。
好在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妥协,“瑶子改变了主意,签了合同,拿了钱”。
刘柠